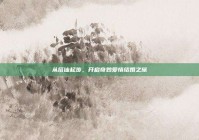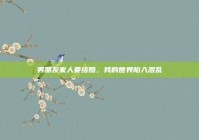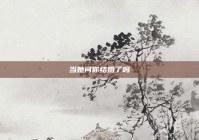结婚时牧师说的誓词,半路夫妻该如何相处
结婚时牧师说的誓词,半路夫妻该如何相处?
通常人们把二婚的夫妇称作半路夫夫妻,近些年来,随着离婚人数的攀升,咱们所说的半路夫妻也在增加,有很多人不看好半路夫妻,认为半路夫妻幸福的不多,痛苦的多。其实笔者并不这样认为,你要夫妇双方处理好关系,同样能够过的幸福。
话说的话:“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如果夫妻一条心,能够做到以下几点,也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

半路夫妻都有自己的孩子,人的本性都是好的。但谁都会有自私的一面,在对待双方孩子的问题上,一定要做到公平同等对待,以心换心。如果在孩子的问题上处理不好,会很大地影响夫妻之间的感情,把对方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真诚对待,相互理解和尊重,作为半路夫妻,一定要真诚,第一颗真诚的心对得对方,做任何事都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多为对方考虑,要有共同语言,共同爱好,互敬互爱,共同走完美好的人生。
每个家庭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着矛盾,有矛盾不可怕,只要及时的去化解家庭矛盾。对待双方的子女,要给予更多的关怀。夫妻间要多交流沟通,不要让矛盾累积。
双方对待婚姻一定要慎重,半路夫妻本来就不容易,更要珍惜彼此之间的感情。不能把婚姻当儿戏,夫妻两个人肩负着家庭和子女的责任,过日子就是柴米油盐,要守着平平淡淡的生活。装潢要吸取,婚姻失败的教训,相濡以沫共度一生。
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婚姻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大事,人生苦短,切不可草率,对于半路夫妻,不管怎样走到一起,更要慎重对待,既然有缘走在一起,就要相互扶持相互爱护、相互包容、和和美美的共度一生…
是不是人越大就越难喜欢一个人?
感谢悟空先生邀请!
“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爱”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各种各样的“爱”,随着年龄增长会自然而然的发生。男女之间的相互倾慕,俗话说“对上眼”,称之为“爱情”。“爱”的发生在每个阶段感觉是不一样的。懵懂阶段。每个人的青春期都会有自己倾慕的对象,称之为“喜欢”更准确。这个阶段是一种无任何杂念的“纯粹喜欢”。“女孩,长的好看,清纯”,“男孩,高瘦帅气活泼”,是“喜欢”的标签。认知成熟阶段。上大学前后,这个阶段,对“爱”区别于朦胧的认识,身体与认识相对成熟,但又没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对男女的感情与接触非常好奇,在交往和认识上,均上某个点打动了自己,或者因某种兴趣而在一起。女孩飘逸的长发,男孩打球的姿势,都是为之动情的“标签”。结婚前后阶段。找对象,结婚生子,人生的重要时刻,炽热的青春爱情,即将用“家庭”的形式来表达。婚姻殿堂,是用“爱”的誓言和“相守一生”来编织的。家庭生活的阶段。家庭,是用“责任”来维护的,你的重心,不止于对妻子的“爱”,更表现在孩子成长、照顾老人。年龄增大的阶段。随着年龄增大,爱的范围已经转化,爱的能力也已聚焦。曾经的“爱情”,已经在日积月累的岁月中抹平并沉淀,“亲情”已经占据了你的全部。爱已成“习惯”,爱已成“定势”,你已缺乏重新“爱”的勇气与“决心”,你更大心思在于社会、事业,因为,在“爱”上,你已心安。你听过最伟大的爱情宣言是什么?
这个问题没有人回答,我来答。
“爱情”是不需要用语言表达的,它是用时间和行动来验证的,说的再好听,没有行动等于零。
从古至今,多少感情熬不过时间,熬不过金钱。不管什么年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不是拜金,而是生活就是这样,谁都想过得好点,快乐一点,幸福多一点,烦恼少一点,一个连自己的温饱都解决不了,语言表达再好,有意义么?所以说男人也罢,女人也罢,男生也罢,女生也罢,只要确认自己是真爱了,就付之于行动,行动是无声的语言,也是最好的表达!是否认同😄
一生只送一人的结婚戒指?
提起婚礼首先让人想到的就是婚纱、教堂、牧师、宣誓,姑娘们对婚礼和白纱都充满了向往。如果问女孩最喜欢的是什么衣服?肯定是白纱,最喜欢的配饰也莫过于戒指,其实这些都是源于西方国家,并在中国大肆流行。同样,戒指也是同西式婚礼一样流行于中国。在西方婚礼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戴戒指。那么,结婚戒指戴哪比较合适呢?
1、戒指的起源
现代社会中戒指在年轻人心中占据这么大的位置,那么戒指是如何流行的呢?戒指最早起源于古埃及,埃及人用小圆环表示永恒,他们想用小圆环套住爱人一生一世。从最初简单的小圆环,到如今风格款式材质各异的戒指,变得是材质,不变的是爱情。或许很多人不知道戒指起源于哪里,可说到戒指的意义,大家必然都能想到爱情。
2、戒指的价格
明星们爱钻戒超过了其他所有珠宝首饰,从明星钻戒价位里就可看出。李嘉欣的5000多万,章子怡的3000多万,大S的2000多万。不过,戒指却并非是明星人士的专利。普通人一样可选择戒指。一款设计出众,工艺卓越的戒指不一定就非常昂贵。比如乐维斯,钻戒一生只送一人,代表着一生只爱一人的承诺,让年轻人动容。而“以我之名,冠你指间;一生相伴,一世相随”的承诺更成了无数年轻人心头最爱的结婚誓言。
3戒指的佩戴
关于戒指的戴法,西方国家是将戒指戴于左手无名指,因为西方人认为左手无名指是离心脏最近的地方,而中国,则是男性将戒指戴于左手无名指,女性则戴在右手无名指。不过,90后们遵守男左女右的比较少,他们更愿意完全国际化,所以,无论男女都是左手无名指。
戒指有多重要?它代表了这世上密不可分的一对恋人,代表了彼此忠贞的爱情承诺。从大家对“结婚戒指戴哪”这个问题的关注就可看出人们对戒指的看重。说白了,只要两个人感情在,无论戴在哪个手指上都不会被嘲笑,因为爱情才是这场婚姻里的主角。
唯一卸任后再度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是谁?
随着拜登入主白宫的日期临近,关于特朗普未来的动向引发普遍关注,鉴于他永不服输的性格和对2020年大选结果是否公正持严重怀疑态度,因此有许多人预测,特朗普很可能会在3年后再度出马竞选总统,以一雪前耻。其实,总统下台后再度通过竞选上台的现象,在美国有先例可循,但迄今为止也仅有1例。此人,便是美国第22任、24任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
01 初主白宫
克利夫兰,1837年生于新泽西州卡德维尔一个公理会牧师家庭,1859年考取律师资格,此后在布法罗做律师,并在数年后以民主党人的身份踏入政坛。1881年,克利夫兰竞选布法罗市长成功,次年又成功地当选为纽约州长,由此成为全国关注的政治人物。在担任市长、州长期间,克利夫兰将“政府机关应该得到公众的信任”作为行动口号,推行一系列惠民政策,并严惩贪污腐败现象,由此获得大批选民的拥护。
克利夫兰旧照
1884年,拥有超高人气的克利夫兰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并在当年11月的大选中战胜共和党候选人布莱恩,以47岁的年纪当选为总统。克利夫兰就职后,把他在布法罗市长、纽约州长任上形成的执政风格带入白宫,在机构改革、关税纷争、工人罢工等诸多难题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强制推行文官制度改革,借此罢免近10万共和党人的官职,并换上民主党人。
克利夫兰第一次就职典礼
克利夫兰的改革虽然取得非凡成就,但在很大程度上加深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对立情绪,激化了社会矛盾,使得整个劳工阶层都站在他的反对面,对其竞选连任极度不利。果然,在1888年的大选中,克利夫兰以微弱劣势败给共和党候选人小哈里森,并在次年3月黯然卸任。不过,克利夫兰并不打算退出政坛,而是在离开白宫前发下誓言,宣称自己在4年后一定会实现“王者归来”。
02 王者归来
克利夫兰并不是“嘴炮”,早在败选的当天开始,便积极筹划再度竞选的事宜,并得到大批对共和党政策不满者的拥护。1892年,克利夫兰一路上过关斩将,在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后,最终又在11月的大选中,完胜因强推《麦金利关税法案》而成为众矢之的总统小哈里森,如愿以偿地实现再度入主白宫的梦想。由此,克利夫兰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位在下台后再度当选的美国总统。
克利夫兰与家人的合影
克利夫兰在第二个任期内,为解决由费城雷丁铁路公司破产而触发的金融风暴,宣布恢复金本位制、向大财团举债,并动用军队镇压铁路工人在芝加哥举行的大罢工。然而,这些举措并未取得积极成效,并在很大程度上激化社会矛盾,为克利夫兰招致普遍的批评,而来自劳工界的谴责尤其激烈,对他的形象无疑构成致命伤害。
与此同时,克利夫兰在对外政策上一改美国的保守主义传统,而是采取相当积极的姿态,追求扩大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势力范围,并谋求向远东及太平洋地区进行经济扩张,以此来适应垄断资本主义的大发展。虽然克利夫兰的进取政策为美国带来现实利益,但爱好和平人士却对此深恶痛绝,并送给他一个“好战总统”的称号。
克利夫兰是唯一卸任后又当选的总统
1897年3月4日,克利夫兰结束第二个任期,此后返回新泽西州居住,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和1家人寿保险公司任职。由于任期并不连接,加之推行的政策饱受争议,因而历史学家对克利夫兰的评价并不高,甚至称呼他为“虎头蛇尾”总统,但克利夫兰对此却并不认同。1908年6月24日,克利夫兰因心脏衰竭去世,终年71岁,临终遗言是“我竭尽全力做到问心无愧”。
03 砖家说
虽然所处时代不同,克利夫兰跟特朗普的遭遇却颇有相似之处,他们在第一个任期内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取得过非常出色的成就。然而,由于他们的性格过于刚强、做事雷厉风行,不懂得党派合作、妥协,加之某些政策极具争议性,因此造成朝野对立情绪明显,社会矛盾被严重激化,从而让他们以微弱劣势憾失总统宝座。
特朗普能否成为“克利夫兰第二”
不过,克利夫兰并未因连任失败而意志消沉,而是深刻总结、吸取失败的教训,在此后4年间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并提出更能吸引大众、更加切实可行的竞选纲领,由此实现“王者归来”的终极目标。对于心高气傲、绝不轻言失败的特朗普来讲,克利夫兰堪称他的榜样,只要他肯踏踏实实地做出改变,4年后未尝不能复制克利夫兰的成功。
参考书目
亨利 · F · 格拉夫 (美):《独立与诚实:格罗弗·克利夫兰传 》,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林涛、裴迎钦(中):《美国总统全传》, 时事出版社 2004年版。
-
上一篇
恋爱十年,要是过了10年以后 -
下一篇
西方婚礼最正确誓词英文版,2020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