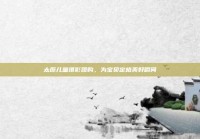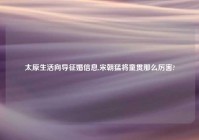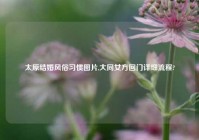太原征婚,你听说过哪些骇人听闻的真实事件?
太原征婚,你听说过哪些骇人听闻的真实事件?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忻州市发生了一起几乎灭门的辐射案件,此事甚至惊动了国务院,而作为事发地的忻州南关一时间人心惶惶,谣言满天飞,以至于商店停业,学校停课……不过幸好国家处理及时,辐射源被很快找到收回,这才将此事完美处理。

1992年11月19日,忻州本地人张有昌比往日回家要早得多,他告诉刚娶过门不久的妻子张芳说自己恶心、呕吐、肚子疼,并带有掉头发的现象。妻子见他病情严重,就与他一起去忻州市人民医院去就诊。
在经过常规的化验检查后,医生们经过会诊也无法确定他的病因,所以建议他住院治疗以便观察。由于妻子张芳已经怀有身孕不便在医院照顾丈夫,于是便将丈夫的大哥张有双叫来医院陪护照顾弟弟,而自己则回家休养去了。
然而,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事情过去了两三天,11月21日,住院的张有昌病情不仅没有什么起色,就连来陪护他的哥哥张有双也开始有了脸色发紫,呕吐不已的症状。
局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医生们判断这很可能是一种未知的传染病,就是将兄弟二人转到隔离病房继续观察。但是按照传染病对他们进行治疗,兄弟二人的病情仍然没有丝毫缓解,于是医生建议他们医疗条件好一点的太原就诊。
11月24日,在张有昌的父亲张明亮和岳父张丑寅的陪伴下,兄弟二人转院到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作为从未见过的病例,专家们对他们作了全面检查,最后会诊的结果是其症状符合“辐射病”,按照规定,具有辐射性质的病例是要上报省卫生厅的,于是专家们将会诊结果上报了省卫生厅。
然而山西省卫生厅接到消息后,通过调查得知忻州不存在任何放射源,于是兄弟二人“辐射病”的结论被推翻,这就相当于兄弟二人的病情仍未确诊。在此期间,张有昌的头发大把大把脱落,腿部呈现了深紫色,山大一院对他们作了重新检查,仍然没有搞清楚病因。
由于家庭的拮据,张家负担不起医院昂贵的费用,于是张家人商量了一番,决定回到忻州静养观察。
然而,这个怪病是无情的,它来势汹汹,根本没有给人反应的机会。12月3日,弟弟张有昌离世;12月5日,哥哥张有双离世;12月7日,父亲张明亮也因同样的病情一病不起,在12月16日临终前,他将家中所有的积蓄两千元钱交给怀孕的张芳,让她去北京的大医院求诊,说道:“我们死也要死个明白!”
此时的张芳已经有了张有昌开始发病的症状,正当她惶恐不安,茫然之际,她父亲张丑寅下了决断,当天晚上便带着她登上了去北京求医的火车。
12月17日,24岁的张芳辗转于北京各大医院,但经过检查张芳的白血球数量不及平常的十分之一,已经属于危重病人,大夫们推荐张丑寅带着女儿去以治疗血液病著称的北京人民医院就诊。
怪病的确诊12月18日,张芳被送进了北京人民医院,当时的诊断为“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但本着对患者高度负责的精神,张芳的病历来到了中国著名的血液病专家陆道培教授手中。他亲自过问了患者家属后,得知已经有三人死于同样症状,于是心中敲响了警钟。
下午三点,陆道培教授邀请了解放军军事医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的毛秉智教授、放射病血液科的专家黄世敏、北京朝阳区医院传染病所所长、环境检查总站副部长王功鹏等人对张芳作了会诊。尽管最后有些分歧,但毛秉智教授和陆道培教授认为,张芳的症状虽然类似于诊断出的“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但这种病症不可能同时短时间内造成数人死亡,应该属于辐射病,但病发地忻州地区并没有辐射源,所以这为确诊带来了困难。
为了进一步研究张芳的病情,陆道培教授在12月24日又邀请了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所长王作元、白玉书等数名研究员再次进行了会诊,这三位专家听取了病人的情况后,对张芳采取了血样进行染色体筛查。实验结果表明,张芳的细胞畸形体比例高达44%以上,高出正常人的数万倍,从这个结果来看,患者是肯定受到了过量的电离辐射造成。
专家们对张芳的病情确诊了以后,所以认定其他的三位死者也是死于“辐射病”,于是将该情况向卫生部作了报告,卫生部认为事件严重,于是向中央作了汇报。
12月31日,国务院徐副秘书长作出了重要批示:“除抓紧对张芳检查治疗外,应集中力量尽快找到放射源。”其他领导也电令山西省政府尽快予以查清、解决!
一场轰轰烈烈地寻找辐射源的战役打响!
辐射源到底是何物?山西省政府对中央的批示十分重视,当即组成了事故调查小组,忻州市政府对事故的调查和处理工作展开了积极的配合。
要知道,辐射类物品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严格管控的危险品,所以追查的重点就在于忻州市在什么时候出现过辐射物。经过溯源,辐射物的源头很快就被确定出来。原来忻州曾在1973年9月从上海医疗器械厂接收过一批钴60的辐射装置,被安置在当时的辐射室中,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又被划归给环境检测站。
1991年环境检测站扩建需要拆除放射室,那么里面的钴60辐射源需要移交给山西省放射性废物库收储。对于钴60这样的放射物的转运工作,国家是有着明确规定的,必须由专业工作人员来实施。按照规定,忻州市政府从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请来了两位专业人士来做转运工作。
1991年6月25日,两位专业人士对存放于废井底部的钴源作了倒装收贮工作。由于年代久远,忻州市科委提供的钴60辐射源的数目为五只,所以两位专业人士在找到五只辐射源后也再未寻找。但实际上,当时忻州接收的钴60辐射源一共有六只,其中五只是苏联产品,一只是法国产品,科委工作人员误以为只有苏联五只,以至于酿成后来的悲剧。
10月27日,建筑工程队开始对忻州市环境检测站进行施工,当时工程队聘用了忻州市南关村的一些村民对地基进行挖掘作业。10月29日,在挖掘防辐射室的过程中有人挖出一个2-3厘米闪闪发亮的圆柱形金属,张明亮觉得这块金属异常好看以为是“宝贝”,便捡起来放到张有昌的衣袋中,岂不知他认为的宝贝,实则是差点酿成灭门惨案的罪魁祸首。
既然确定了辐射源,下一步就是找到它,否则更多的不幸还会继续发生。于是事故处理小组兵分多路,前后六次对张有昌、张有双以及张明亮的行动轨迹来查起,对张家的左邻右舍,亲朋好友家里逐个排查,最后扩展到整个南关村,就连医院、火葬场、下葬地排查,但仍然未找到这个可怕的辐射源。
寻找辐射源的工作陷入了僵局!
工作组成员提出,要不让当事人详细说一遍当时的情况,或许可以从中抽丝剥茧找到线索,此建议得到了工作组领导的认同,于是连夜赶到北京人民医院找到当事人张芳以其父亲张丑寅与之谈话,让他们事无巨细的将当时发生的情况介绍一下。
果不其然,在张丑寅的回忆下,终于想起一个细节。在陪同张有昌去山大一院检查时,曾有一个金属物掉了出来,张丑寅当时问了一下这个东西还要不要,张有昌摇了摇头,张丑寅就将这个金属块扔到了医院的垃圾桶里。
工作组成员反复询问了张丑寅这个金属的模样体型后,基本确定被扔进医院垃圾桶的极有可能就是钴60辐射源,工作人员迅速将此消息通知了远在忻州的工作组领导。
众所周知,医院的医疗废物是有专门的处理地方的,太原的山大一院也没有例外,依照张丑寅所描绘,再加上当时山大一院的垃圾清运工翟金元提供的说法,这枚丢失的钴60辐射源应该在垃圾处理厂。但蹊跷的是,工作组成员携带着探测仪器多次在这个垃圾处理厂进行探测,但没有发现一丝一毫的辐射痕迹,更别说辐射源了。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再次断掉了,辐射源究竟去了哪里?多耽搁一天,或许就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有人提出,听说土渣车为了图方便经常将垃圾倒在野外,那么医院的垃圾清运车会不会也是如此呢?当时的卫生监理处处长曹敏站了起来说道:“我再找院长做做这个翟金元的工作,如果他真的倒在野外,反而更有利于我们处理该辐射源!”
1993年2月1日,曹敏找到院长一同到了翟金元家中劝说道:“如果你把垃圾倒在野外,如果没有造成后果,我们保证不会深究,或许还有一定功劳。但是一旦再次发生辐射事件,你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将是严重的!”在二人苦口婆心地劝说了一顿之后,翟金元妥协了,他将倒垃圾的地方告诉了二人,并带领工作组的成员找到了钴60辐射源,众人纷纷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在公安、卫生、环保各部门的配合下,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的院长带着十几名专家将该辐射源进行了专业回收。要知道,这条路是通往山西有名的景点晋祠的必经之路,过往游人络绎不绝,幸好及时处理了这个危险的物品,否则后果的确不堪设想。
结语因为档案的遗失,工作的疏漏,竟酿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这一小块危险的“金属”让张家几乎灭门,虽然张芳在国家的极力治疗下好转过来,但其肚子里的胎儿却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孩子出生后虽然表面健康,但其心智却远低于同龄人,这个胎儿的不幸也成为我国首例子宫内遭受的辐射病例,同时被国际原子能机构收录。
此事实证明,遭受辐射后的人或物都有着不可预估的后果,所以前些年日本核泄漏之后口口声声称其粮食可以正常食用,国内一部分人员也为其呐喊呼应,这其实完全是在愚弄百姓,要知道福岛周围的农产品就连日本人自己都不吃,为何要出口给外国呢?幸好我国政府对该地区出口的产品控制较为严格,这才没有大量流入中国市场。
逝者已矣!但是活着的张芳和女儿张京生不仅要忍受连失亲人之痛,还要忍受着辐射带来的后遗症,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对于辐射类的危险物一定要严格管控,工作要细致谨慎,更要对普通民众普及基础的防辐射基础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悲剧不再重演!
参考资料:《环境保护事典》等
老年人丧偶之后找了一个老伴但是不想办结婚证?
我认为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说说我的伯父吧。
我的伯母是2001年去世的。伯母走后,家里就只有伯父一个人,四个子女都已经成家,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各有各的工作,都不在身边。
伯母走了一年后,伯父的精神状态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以前见了我都是有说有笑,再见了我只是礼貌性的点点头。院子里,没有那么有序了,农用工具横七竖八的放着。屋子里也没有了以前的整洁,日常用的东西凌乱一堆。
又过了半年,伯父的几个子女,通过给伯父做工作,商量着给伯父找了个老伴。在这件事情上,就看出伯父的老谋深算了。
几个子女,通过红娘,给伯父提供了六、七个人选,当然,伯父的经济条件摆在那里。最后,伯父相中了一个年龄比自己小五岁的老伴,对方是丧偶,一生没有子女,只有两个娘家侄子。
伯父自己选了个日子,在酒店摆了三桌,让双方家庭亲近的成员都到场,相互认识一下。也没办结婚证,这权当迎接老伴的一个仪式吧。
伯父之所以选择这种情况的老伴,主要是对方没有子女,也没有什么牵挂,也不会有什么财产上的纠纷。在一起后,彼此能舒心的过日子,老伴也不会有三心二意的。
在伯父去世的前一年,把老伴的户口迁了过来,也办理了结婚证。一是感情成熟了,都彼此适应了。二是以后要拆迁的话,也少了一些麻烦,也给老伴留下了一份补偿。
自伯父走后,四个子女对待伯母和亲妈没有什么不同,隔三差五的经常回来,给 伯母要么留下足够的生活费,要么把柴米油盐买全了。我偶尔回家见到现在的伯母时,总是满脸笑容,开心的和我聊一会儿。
其实,老年人找老伴,也要尽量找适合自己的,少一些纠纷和闹心,多一些开心和舒心。老了不就是图个快乐嘛。
你听过什么有趣的吹牛故事吗?
朱麻二修湘渝铁路回来,就当我们的生产队长。开会讲话,时常是抛出一个论点,接着搬出实际事实加以佐证,要仔细听,才能发现是在吹牛:
朱麻二讲:“朋友在精不在多,朝庭有人好办事。
“修湘渝铁路那阵,和我同睡同起同做事情的,一个四川达县的朋友,铁路完工了,就被调去当火车司机开火车。
“那天,我挑一担东西,在铁路上走被他看见,他马上把火车刹下来,下车来亲自把东西提上驾驶台,把我带到了前面的目的地。”
有社员当场表示疑惑:“火车可是分秒必争的玩意儿,他这一停,整条铁路不是全都乱套了?他不是被劳改就是遭枪毙。”
朱麻二会上发火:“你晓得格锤子:这条铁路搞调度的,是他的妹夫,妹夫的姐哥,又是铁路局的局长,谁拌得歪我这个朋友?!”
公社在外地,引进了一批良种冬瓜幼苗,强制给每个生产队分配了栽植任务。
在动员大会上,朱麻二讲:“这种冬瓜,我修铁路的时候看见过。
“大得很,最小的冬瓜,直经也有两米六尺高,热天可以一家人,搬板凳儿进去坐起乘凉。
“而且,这种冬瓜一次栽种终身受益:想吃冬瓜了,就去切一半截来抬回去,地里那一截,一晚上就长出来,和原先一模一样。
“那次我在冬瓜里乘谅,一睡醒来发现冬瓜长拢来把我吞了,吓得我用板凳,把冬瓜打一个洞才出来了。”
七九年打越南,我们公社出了一个,炮兵一等功臣秦y堂,一时间,家乡政府宣传他的英雄事迹,成了工作的重中之重。
又是在社员大会上,朱麻二说:“秦y堂有哈一口气炮弹转弯的本事,总指挥许世友,亲自坐直升飞机到前线去看真假。
“恰好敌人发起了冲锋,把秦y堂的副炮手弄牺牲了。
“秦y堂很着急,也以为新来的是炊事班的老兵,就吼:老头儿站起干啥?还不赶快去给我装填炮弹。
“许世友光着膀子就上,手法比专业炮手还专业。
“一时间,许世友装弹,秦y堂哈气,不管越南人藏在哪里,炮弹就象长了眼睁,拐弯就到。
“战斗结来,秦y掌得知,被他熊过的老头儿是许司令,当时就吓了一个激灵。
“许司令却说:不给你记一等功我不姓许。”
清末四大奇案之太原奇案?
一
话说在鸦片战争打响的这一年春天,大清帝国还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在山西太原的阳曲县,却出了一桩奇案。其中的情节曲折离奇,确实可以称得上清末四大奇案中情节最离奇的一个。
1840年春天的一个清晨,在阳曲县城郊的一个村口,一位勤快的村民来到井口挑水。他发现打上来的井水呈淡红色,透着一股血腥味。他把头伸向井口望下去,却依稀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影子。
于是他连忙找来了地保和村民,他们把带钩的绳子放入井中,竟然拿上来一具尸体,身穿青袍,脖子上中刀。地保和第一个发现的村民连忙一起到县衙去报案。
经过仵作的验尸,发现这个死者应该是一个和尚,头上有戒疤。阳曲县县令杨重民就派出衙役到四周的寺庙去盘查,崇善寺的主持认定这是半年前从河南来的青壮年游方僧人。前几天离开寺庙外出化缘未归,走的时候穿的是僧袍,而不是青衣。
二
和尚所穿的青袍就成了本案的重要线索,县令就决定从这件衣服开始查起。很快就有人证实,这件青袍是城外开豆腐店的老汉莫老实的衣服。莫老汉每天向城内送豆腐,经常穿这件衣服。
杨重民就派出衙役把莫老汉带到县衙问话,直接莫老汉神情慌张,说话吞吞吐吐,前言不搭后语,很多地方自相矛盾。杨重民就决定审讯莫老汉,打开这个突破口。
莫老汉在公堂之上马上就说出了真相。因为自己家拉磨的驴子被租借了出去,他只好自己亲自天不亮就开始磨豆腐。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门声,原来是一个身穿凤冠霞帔的新娘。
来人刚一开口说话,却是男人的口音。他自称自己是一个和尚,莫名其妙就被别人穿上了这样的衣服。为了能够回到寺庙,希望向莫老汉这一套衣服穿上,这身凤冠霞帔就送给莫老汉了。
三
说到凤冠霞帔,马上又引入了另外一个悬案。县令杨重民马上想起前几天,本县两个富豪曾经到县衙来告状。原告是土豪姚半城,状告富商张百万。
姚半城和张百万两家早年儿女有婚约,姚思孝正准备迎娶张百万的女儿张玉姑。突然张百万却告诉姚半城,女儿暴病而亡,尸体也不翼而飞,连同陪葬的凤冠霞帔一起不见了。
县令马上让衙役到莫老汉家找出了凤冠霞帔,叫来张百万辨认。张百万说这确实是自己女儿穿的凤冠霞帔,但他的证词前后也出了问题。在县令的逼问下,案情又出现了重大反转。
张百万说,女儿放过的尸体并非被人偷走,而是在棺材中诈死了。当天晚上,在院子里值班的下人看到玉姑从棺材里跳出来,冲出院子跑了。张百万认为这非常不吉利,就对外谎称是女儿的尸体被人偷走。
四
县令杨重民决定把这两个案子合并审理。结合张百万的推理和供词,他们将案情进行了推演,认为是莫老汉碰到了诈尸的张百万女儿,偷走了凤冠霞帔。正在这时被和尚撞破,莫老汉就把和尚杀人灭口,把尸体抛进了水井之中。
在审讯中,莫老汉高喊冤枉,拒绝承认。但在县令的刑讯逼供下,莫老汉被屈打成招,只好承认了所有罪状并签字画押。案情到此告一段落,案卷被呈报刑部核准。
不料在12天后,却突然有人来县衙击鼓告状,为莫老汉喊冤。来人自称叫曹文璜,是张百万女儿玉姑的丈夫。县令心中暗暗称奇,玉姑的丈夫难道不是姚思孝吗?
曹文璜称,玉姑现在还活着,两个人只不过是私奔而已。县令连忙把张百万叫过来问话,这就牵连出一桩陈年往事。曹文璜和玉姑早就定下了娃娃亲,两个人青梅竹马。后来曹家道中落,嫌贫爱富的张百万就把女儿许给了姚家。
五
就在姚思孝准备娶玉姑的时候,曹文璜决定和玉姑两个人私奔。在丫鬟的帮助下,两个人在结婚的前一天逃出了张府。原本两个人准备先去玉姑的大姐金姑家暂避一时,但金姑不开门,两个人只好离开。
半夜他们走到城外,来到了磨豆腐的莫老汉家。最终租借了莫老汉家的毛驴,曹文璜送自己的新娘子回老家。把家中的事情都安排好后,曹文璜现在来归还莫老汉家的驴子,才引发了告状的一幕。
县令马上就明白了,张百万彻头彻尾在撒谎。在正准备对张百万用刑的时候,他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当女儿逃跑后,张百万就带着家人追的出来。
张百万认为小女儿很有可能会去大女儿家,就追了过来。金姑守寡了好几年,磨磨蹭蹭过了很久才过来开门。开门后神情比较慌张,金姑不承认玉姑藏在自己家中。
六
张百万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只有金姑家的箱子没有打开搜查。但金姑说箱子的钥匙丢了,张百万就认定玉姑就藏在箱子里,命令下人把这个箱子抬回了张府。
张百万回到家中后,打开箱子却发现是一个死了的和尚。情急之下张百万就谎称女儿死了,把和尚的尸体穿上凤冠霞帔放进了棺材。结果和尚只是晕了过去,醒来后就慌忙冲出了院子,逃跑了。
和尚来到了莫老汉家中,用凤冠霞帔换了青衣长袍,就离开了莫老汉家返回寺庙,却最终离奇的死在了村口井中。和尚到底是谁杀的?案子中未解的谜团,还要不要调查下去?
县令杨重民感到了莫大的压力,他已经将案卷呈报刑部。如果现在推翻之前的结论,那么极有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仕途。他决定绝对不能翻供,就把曹文璜定为莫老汉的杀人帮凶结案。
七
这时新任太原知府刚刚上任,新官上任三把火。他认为这个案子中间的疑点很多,比如重要的证人金姑和银姑都没有出庭作证。再者莫老汉60多岁,是怎么杀死青年和尚的?
经过讯问,金姑承认和尚是自己的情夫。在张百万搜查房子的时候,只能把他藏在箱子里。玉姑说自己和曹文璜到莫老汉家时,并没有看到和尚。太原知府认为,根据尸检报告,杀人者手法纯熟,肯定是一个老手,并且用的是短刀。按照这个思路,安排进行了新一轮排查。一个新的消息传来,就在死人的这一天,现成的一位吴屠户突然失踪,但有人在晋祠老乡看到过他。
知府马上派人把吴屠户抓了回来,经过审讯最终才真相大白。这个和尚原来是个花和尚,在回寺院的路上,又去了自己的相好吴屠户娘子家中。吴屠户回家发现了两个人的偷情,就杀死了和尚,并把他抛尸井中。
这个案件在华北大平原上传得纷纷扬扬,连慈禧太后都听说了大为感叹。吴屠户以杀人罪被判决秋后问斩,杨县令因草菅人命被革职查办,曹文璜和莫老汉被无罪释放。曹文璜和玉姑两个人有情人终成眷属,夫妻双双把家还。
我想知道历史上有什么稀奇古怪的故事?
这个人的人生,简直就像是小说里穿越到清朝,开了现代外挂的主人公,虽然他确确实实存在于历史里,但是却没多少人真的认识他,堪称“稀奇古怪”!
“落榜”的学霸——徐寿徐寿,号雪村,出生于1818年,也就是嘉庆年间江苏无锡的一个没落地主家里。5岁那年,徐寿的父亲去世,家境更是雪上加霜。徐寿的母亲就对徐寿十分严格,希望他能考取功名,好光复门楣。徐寿因此从小饱读诗书,十分争气,连邻居都夸赞不绝,活生生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不仅饱读诗书,徐寿还喜欢手工,经常天马行空地“创造”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这样活泛的思想在当时有些格格不入,尤其是他将面临的科举考试,八股文的固定思维让徐寿十分痛苦。果不其然,他连当地的“童子试”都没通过,让母亲大失所望。
“尝一应童子试,以为无裨实用,弃去。”
徐寿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跟科举没什么缘分,于是索性不再赶考,不久之后,徐寿的母亲也去世了,徐寿因此更加专心投入到科学创造中去。在这期间,他博览群书,创造出自制指南针、象限仪、自鸣钟等等,这样精巧的手艺,让他无意之间认识了同是“科学发烧友”的华蘅芳,两人就像是“学霸组合”,从此,在清朝的科学界大刀阔斧地施展自己的才华。
全能手艺匠人+细心理论家+金主外交家组合话说徐寿和华蘅芳结为知己,两人经常一同“淘宝”,发现那些知识点丰富而独特的书本,都会买下来细细研读,比如看到一本《博物新编》,两人不仅读了很多次,还亲自动手实践,想要做三棱镜的光学实验,华蘅芳二话不说回家取了祖传的水晶图章来磨镜。还有很多西方的新奇事物,他们俩也时常一一去了解看透。
过了不久,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西方列强的侵入让清朝不得不自救,发动了洋务运动。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徐寿和华蘅芳陡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才。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聘请徐寿和华蘅芳来设计军械。
两人经常跑去看洋人的蒸汽机和轮船构造,久而久之,心里也有数儿了,徐寿就自己动手,一样样地制造零件,华蘅芳也用自己的“数学技能”来帮他画图、计算等,曾国藩则利用自己朝廷大臣的身份,为他们拉资金等。
就这样,当年的艰苦环境下,1865年,中国人还是造出了第一艘蒸汽机明轮船——黄鹄号,其中的蒸汽机几乎是纯手工制作,堪称神奇。同治皇帝御因此赐给徐寿一块“天下第一巧匠”的牌匾。
随后,徐寿又接着制造出中国第一艘明轮兵船“恬吉号”,从各方面碾压当时的日本。日本的第一艘国产轮船——千代田号,马力只有64匹,而恬吉号的马力高达392匹,这样一对比,就能看出徐寿制作的轮船到底有多厉害!
1869年,徐寿设计并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螺旋桨轮船“操江号”。只可惜,光绪二十年被日军俘获,操江号是最后一艘退出使用的北洋舰队军舰。
总而言之,徐寿领衔下制造出的轮船和蒸汽机,让中国勉强地跟上了当时的世界工业发展的脚步,甚至支撑着岌岌可危的清朝与列强的战斗。
引入西方科学知识的领头羊徐寿不仅仅是一个手工匠人,他目光长远,希望先进科学的理论知识能传遍中国。只可惜,当时的朝廷无心再扶持这种长期投入的“项目”,国人又被八股文思想腐蚀深刻。
但徐寿没有放弃,他和华蘅芳、以及西方传教士傅兰雅联合创建了月刊《格致汇编》,用来传播西方科学知识。
随后,徐寿又和时任英国驻沪总领事麦华佗联合创办“格致书院”,是上海近代第一所“中外合作学校”。
这些还不是徐寿最著名的贡献,现在初中生高中生们人人都得背诵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也是徐寿的“作品”之一,你们知道吗?
徐寿想把西方的化学元素周期表翻译成中文,像日本,他们的化学元素周期表每个元素都是直接将希腊语音译成日文,每个元素都长长的一串名字,十分晦涩难记。而徐寿想出来的办法,就是直接将每个元素的发音首音节音译为中文,一些金属元素,就在中文加个“金”的偏旁。这才让我国的化学元素周期表大大简化。
1881年3月10日,英国著名科学杂志《NATURE》上出现了一篇题为《声学在中国》的文章。这篇文章不是徐寿投稿,但是作者转载翻译了徐寿的文章,其中他对传统声学定律“空气柱的振动模式”(即伯努利定律),提出质疑,并用现代的科学矫正了一项古老的定律。
因此,徐寿被公认为是第一个在《nature》上发表期刊的中国人。在当时简陋的科研环境下,前辈尚能在世界高知面前展露头角,实在令后人自觉赧颜。
中国的“诺贝尔”——徐寿的儿子徐建寅1884年,徐寿在格致学院逝世,他的儿子徐建寅接过先父的遗愿,继续为中国科研发展而努力,被人赞誉:“一人足抵洋匠数人”。
他在千百次失败中,终于研制出硫酸,从此,外国再也无法垄断我国的硫酸市场。
徐建寅还亲自去欧洲为北洋水师买下了定远和镇远舰,成为甲午战争的主力舰。
随后,张之洞安排徐建寅去钢药局去研制炮弹,这是徐建寅最擅长的领域,他深知责任重大,于是事必躬亲,甚至亲自试炼火药。终于在一次“无烟火药”演示中,突发意外身亡,最后尸身无存,全身只找回了一只穿着大清官靴的脚。
结语徐寿出生在封建和落后的清朝,却偏长成了极具眼光和智慧的“现代人”模样。阅览徐寿的一生作为,真的有一种“穿越者”的震撼感,不可谓不稀奇。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更多有趣内容欢迎点赞关注@天山灵知,与你一起阅读,一起思考!
-
上一篇
越南婚介,你受到过婚骗吗? -
下一篇
辽宁同志聊天室,那些年见过的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