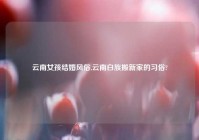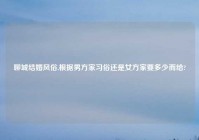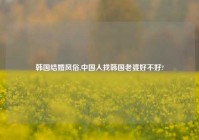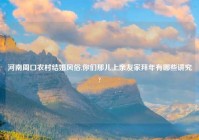南方结婚风俗流变(为什么故事里经常有女娲后人却鲜有盘古后人)
南方结婚风俗流变,为什么故事里经常有女娲后人却鲜有盘古后人?
盘古是混沌第一人,他开辟天地后就死了,身躯化为万物,就他一个,哪来后代。至于女娲,这个就和混乱的中国神话有关了(其他国家也有混乱的,我们不管,我们说我们自己的),有些传说是女娲和伏羲都是人首蛇身,他们是亲生的兄妹还是姐弟,两人诞下后世人族(那女娲补天死去伏羲跑哪去了?)另一说,女娲造人后死去,伏羲自然也是其中之一,而这女娲后人是小说故事影视作品编造的,我们全是女娲后人。其实女性神灵是比较早出现的,毕竟人类最初是母系氏族,而盘古等大神是后世父系社会造的神。可能有些不对之处,算是抛砖引玉。
那是因为女娲在传说中就是人首蛇身 相关游戏《仙剑奇侠传》中的女娲 神界因盘古身体崩解而成型之后,由于天地五灵清浊之气失衡,神界三皇(仙剑中指:伏羲、女娲、神农)经过商议,制定了一整套解决天地间灵力失衡的方略。 伏羲被推举为"天帝",在神界推行等级制度,以约束神的行为,并限制新神的产生,同时制定天规天条,以开除神籍惩罚违规之神,以保证神界消长之平衡。 女娲进入人间,以泥土为材料,以神为参照,辅以少量灵力,创造出比神低等的生物--人和兽,因神界之神有人型、兽型,因此在人间也有人有兽。 因人兽寿命有限,因此拥有阴阳交合繁衍的能力,并在大地之下营造了"鬼界"作为轮回的中转。 神农则在人间遍植草木,作为人兽的食物来源。人被赋予智力,兽被赋予体力,共同享有草木资源。 天地开辟以后, 半蛇女神 ——女娲创造人类;每当妖魔肆虐,莫不挺身拯救万民。有一回,人不敬天招惹天怒;天帝遣诸凶星、恶神下凡兹扰四方,又令共工发天河之水淹灭神州。四方诸神纷纷避走天界,唯女娲独留人间,力阻诸诸神魔贻害人间。女娲身披红衣,手持蛇杖奔走四方, 杀共工止洪水,斩玄龟补天柱, 降青龙伏白虎,逐凶星除恶神,终而四方平复。天帝恼怒,愤而断建木之丘,绝通天之梯;从此,女娲及诸凶星,再也无法回到天界。千百年后,四方神州的百姓,未再遭受神魔们的迫害,人们已经淡忘了这位女神的存在,但是,这位半蛇女蛇的传说,仍然在南方的苗族之中流传着。 仙剑中的诗句: 蛇纹之姬,圣灵之身。 西疆斩风魔,东海杀雷神。 南山收土妖,北荒伏火怪。 终以平水患,而大地重生。 【仙剑奇侠传】 三之中女娲后人紫萱,其与林业平之女林青儿,嫁给南诏国国王,生下赵灵儿,赵灵儿嫁给李逍遥,生下李忆如。 女娲一族虽是神族,但是只要生下孩子就不能长生不老。女娲一族常驻南诏国,有历代圣姑保护。 神下界之后被人间的污浊之气影响,会变成妖的形态 传说中女娲、伏曦都是半人半蛇,还有很多也是,详见《山海经》,但是据考证所谓的半人半蛇其实是古人对影子的理解问题,他们看到的半人半蛇其实是人和影子。 从文化源流上说,在中国古代传说中,蛇通常是灵异魔力的象征。在中国远古神话中,诸神的手臂、耳朵或其他一些部位经常盘绕着某种蛇形,这恐怕也是东方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例如,印度最高的创造神梵天的坐骑就是一条巨大的蟒蛇;此外,其他一些印度神也与蛇有关。《易经》曰:“尺蠖之屈,以求信(神)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对我们祖先来说,蛇是一种令人敬畏的神秘符咒。古代文献《山海经》、《诗经》、《竹书纪年》、《周易》、《尚书》、《左传》、《楚辞》、《史记》等中,都有关于蛇的记述。根据《山海经》的描绘:疆良口里叼蛇,蓐收左耳露蛇,雨师妾手中耍蛇,神于儿身缠两蛇,洞庭怪神头上顶蛇等等。古代传说中许多赫赫有名的天神还是人与蛇的混合体。汉代艺术作品中,伏曦与女娲是人首蛇身,共工是赤发人面蛇身,其手下相柳也是九首人面蛇身。此外,还有不少神同样是人首蛇身。《海外西经》曰:“轩辕之国,人面蛇身。”教化万民统一华夏的黄帝,就出于人面蛇身的轩辕之国。神农伏羲和炼石补天搏土作人的女娲氏都是人面蛇身;《伪列子•黄帝篇》称:“庖慷氏、女嫡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后来人们还把伏羲和女娲氏连在一起说成是人类的始祖。许多赫赫有名的部族联盟领袖都是龙蛇的后裔。传说中同属于龙蛇族的还有雷神、共工、烛龙等。《山海经•大荒北经》提及:“赤水之北,有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是谓烛龙。”说明烛龙氏族的图腾是赤色的人面蛇身。有趣的是,从原始彩陶和铜器、石刻中,也可以看到这些人面蛇身的图像,甘肃武山县出土的仰韶文化原始彩陶有人面蛇身纹和人面龙蛇纹,商代铜器有《人面蛇身纹卣》。山东、四川等地汉代石刻有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形象。在远古时代,中华地域普遍信奉蛇图腾。数千年各民族的迁徙和文化的融合,从而使蛇图腾越传越广,许多少数民族,如台湾高山族、海南黎族等仍保留蛇图腾的遗迹或习俗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8-10 21:17 《山海经》女娲神话的传承流变 《山海经》被称为“神话之渊府” ,蕴含着丰富的神话资料。由于《山海经》资料来自荒古,其中神话素材便成了后世许多神话的源头。世界上任何民族的神话都经历了许多次变更修改。神话的传承流变主要归功于广大民间口头创作者的辛勤奉献,《山海经》神话也是如此。探讨《山海经》神话的传承流变既有助于当前的“《山海经》神话群系”的传承保护,又可在东西方神话比较研究中充分展示东方《山海经》神话的特色。 西方神话中造物神话和开辟神话很多,女娲神话是东方神话中最著名的造物神话、开辟神话。《山海经》记载的女娲神话文字不多,但却是这一神话的最早记录。《大荒西经》云:“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经文“女娲之肠”,郭璞云“或作女娲之腹”。又云:“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七十变,其腹化为此神。栗广,野名。”又云“横道”“言断道也”。郭氏所释甚是,特别是“或作女娲之腹”更妙。。 女娲神话乃是上古时代母权社会形态之反映。人类早期普遍存在以女性为中心的母系社会形态。女娲在本经中以繁衍人类的创世主形像而出现,女娲另一丰功伟绩“补天”不见于此书,正是本书古朴之处。生殖崇拜应是女权崇拜最早出发点。汉人应劭《风俗通义》所记“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做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即女娲造人,与本经所记女娲腹化十神(人)均反映先民此一思惟水平。 女娲造人神话后来又增添了“补天”内容:《淮南子•览冥训》“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天”。正史《史记》也记载了这一神话,其《补三皇本纪》云:“当其末年也,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能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鳖足以立四极,聚芦夹以止滔水,以济冀州,于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造人和补天,完全是集造物神、开辟神于一身的天神。女性形象的女娲作为开辟神,较之男性形象的盘古为神格的盘古神话应该更为古老正统。 汉代以后,女娲神话向历史化民俗化发展。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多女娲伏羲合像,寓意女娲与伏羲结合繁衍人类。这既是女娲神话的历史化嬗变,也反映了男权思想的确立。至于唐人李冗所撰《独异记》“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咒曰:‘天若遗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既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鄣其面。今时人取妇执扇,象其事也”则是民俗化之使然。 综上所述,可见发自《山海经》记载的女娲神话较之西方造物神、开辟神神话更为丰满光彩。
就感觉一些现代诗很没水平?
感谢题主提问!
其实,我也注意这个问题很久了。我通过以下三个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
第一,古代文言文,一字值千金,非常简洁!我们翻译一篇200字左右的文言文,可能要500到1000字才能翻译完整,才能把文章的主旨表达清楚。所以,这就要求语言的精炼程度更高!比如,现在人说一句:你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古文是这样说的:君问归期未有期!你看,七个字就把整个一句话的意思表达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古代文言的魅力!
第二,古代诗歌对格式、用词、平仄、句式,押韵等等要求更高。古代有诗、词、雅、颂等等,每一种形式的辞赋都有其独特的结构。单独一个诗的结构,还分为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这么多的要求,只有古文那种一字有N多意思的语言才能达到这种要求!
第三,现代人不重视诗歌的发展和继承,而且多以抒情为主!诗歌在古代文人是一种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想表达爱情,写诗。想寄托乡愁,写诗。想叙述一个事件,写诗!想描述一个美景,写诗!…但凡你能想到的,统统都可以写诗来表达作者内心的活动!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人有很多表达精神生活的方式,比如听音乐、跳舞、玩游戏等等,所以就不太重视诗歌了!
以上是我的一些个人观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祈祷]
民间书法的总体水平如何?
魏晋是中国书法的一个转折过度时期,隶书过度到魏碑,到晋代开始出现行楷,再到行书的发展,出现了二王这样的代表。到唐代书法又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楷书日益成熟,出现了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这样的楷书大家。但又不乏有像张旭和怀素这样的狂草大师,使得唐朝书法形成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中国艺术领域留下了璀璨的一页!
为什么感觉养儿防老越来越不现实?
谢谢邀请:
为什么感觉养儿防老越来越不现实?
我认为如果一开始就有养儿防老的旧观念,把生孩子的目地就是为了让他以后赡养自己,这个动机过于自私化,把孩子作为规避未来物质的风险与经济风险的工具,是不可行的。
因为,一旦父母有了这种旧观念,很容易造成自己不思进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女身上,甚至年纪轻轻的把能干的工作也放弃,成天的游手好闲,自己夲应该买的养老保险也放弃了,就是等着儿女给自己养老。
可以说,这样的老人对自己不负责任,更对儿女也不负责任,毫不夸张的说自己的行为已经限制了子女的自由,因此而耽误了儿女的大好前程。
我所见的还不只是一个人,有的老人甚至不让子女去外地上大学,其实就是害怕一旦毕业回不来,没人给他养老的自私行为。
十年前毕业于国家重点学院的小马,被南方一家大型央企挽留,父母为南方吃不上拉条子为借口不让儿子去,选择了家乡的一小县城,结婚生子过着平庸的日子。
现在想起来后悔莫及,可是早已经晚了,养儿防老的观念已经落后于时代了,积谷防饥,不如买养老保险,只有自己有才是最可靠的,儿女有,也不如自己有。
洛邑一直是天下之中吗?
周人的兴起与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寻找立足点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迁都的过程。《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说:“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刘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始营镐京,至于伐崇又作丰邑居之,武王又于丰旁近地二十五里制为镐京,盖其所以迁者以势大人益众不足以容之故也。盖当强盛而为迁都之举,非若后世衰微而后迁也,是故自邰而豳而岐而丰而镐而洛,此周家所以日盛也。至于平王东迁,则沦于衰微矣。”[1]周人都城的迁徙路线大致为自西徂东,沿渭河而下,直达黄河之滨的夏、商故地洛邑(今河南洛阳)。这便使夏商周三代都城的发展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空间上彼此重合。洛邑建都是一次经过周密规划、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建都活动,在西周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洛邑建都问题,学界已有广泛讨论,但对洛邑建都问题的争论焦点及建都意义仍有深入讨论的必要,本文拟就此作一探讨。
一、洛邑建都及其象征意义
考古发掘表明,洛邑一带曾为夏、商故都的所在地,洛邑所在的河洛地区曾是华夏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西周洛邑建都是三代都城的合理发展,也是新王朝重建统治秩序,确立其统治地位合天性与合理性的重要措施。营建洛邑的计划始于武王克商之后,其直接政治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对广大的东方版图的控制。周人由西隅小国突然入据人口众多、繁荣富饶的广大东方,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新的挑战。如何巩固新王朝的政治统治?加强对广大殷商旧地的控制?无疑是西周王朝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这也就是周武王罢兵西归镐京后夜不能寐的原因。《史记·周本纪》载:“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2]据杨宽先生解释,“定天保”即确定顺从天意的国都,“天室”是指祭祀天神的明堂。“依天室”即在新都建筑明堂举行殷礼。[3]未“定天保,依天室”,就无法建立起代表天意的国都,也无法在天室宣布符合天意的法令。
洛邑建都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所谓“定天保,依天室”,就是要确立新王朝“符合天命、代表天意”的统治中心,以“天命”的庄严神圣和“天意”的不可违背性来证明周王朝统治的合天性与合理性。何处建都本是由现实需要决定的,但它却被赋予神秘的天命解释。在这里,洛邑被认为是“天下之中”,是最接近“天室”,最能代表“天意”的地方。“天室”或“天邑”之所在,则对应着“天之中”的北极帝星位置。在上古文化观念里,天空亦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王国,在天国的“三垣”、“四象”、“二十八星宿”中,北极星所处的拱极一带是天球众星环绕的中心。北极星帝为“天之中”,地上的人君既然代表天意统治世间,则亦应如“天帝”择中而居,这样“天之中”与“地之中”方能相互沟通,天子方能受命于天,以“天帝”代言人身份统治世间,从而为王权统治披上神圣外衣。这便使都城地址与自然力联系起来,与支配一切现象的人格化了的力量联系起来。[4]《何尊》铭文中亦记载说:“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此)乂民”。[5]“宅兹中国”,“就是在天下四方的中心,即洛邑营建新都,并以此为中心治理天下民众。“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营”作何解?作“规划”解,还是作“营建”解?这关系到营建洛邑的时间问题。不少文献如《史记·周本纪》、《左传》、《帝王纪》等记载说,周武王伐纣后营洛邑并迁九鼎于洛邑。而王晖先生则考证说,《史记》、《左传》等文献所说武王营建并迁鼎的“雒”(洛)应是“栎”字的声近而讹,其所选并初步营建的应是栎邑(即河南阳翟)并把九鼎迁于此地,因为只有这里才称得上天下之中。[6]但普遍观点认为,洛邑的实际营建者不是武王,武王仅对东都洛邑作了初步的规划,大规模营建东都的活动是在武王之后的成王之时。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营建洛邑,迁移殷贵族,都是在执行武王的遗志。《逸周书·度邑》就记述了武王要在伊洛地区建立新都,并将此事托付给周公的经过。可见武王之世确有在洛邑营建新都的规划,而这一规划的落实,则是在成王之世。
武王灭商后二年病逝,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发生了三监和武庚叛乱。周公东征,历时三年,最终平息了叛乱。经过这次政治危机,西周王朝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加强东方统治的重要性,于是成王和周公遵照武王遗愿,开始在伊、洛河谷地区大规模营建新邑。《史记·周本纪》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7]《春秋传》曰:“成王定鼎于郏鄏(洛邑),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尚书·召诰》和《尚书·洛诰》详细记述了营建洛邑的过程。据《召诰》记载,召公奉成王之命,先于周公前往洛邑“相宅”,等得到吉兆后,就开始勘察规划城邑,并使用众多殷商遗民在洛水入黄河处营建地基。《洛诰》中对周公考察、勘定洛邑城址的情况亦有记载:“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8]即所卜地望在涧水以东至瀍水之东、西两岸而近于洛水者皆得吉兆。可见洛邑的营建事前经过了周密的勘察、设计和规划。另有《逸周书.作雒》载:“周公敬念于后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 又载,“设丘兆于南郊,乃立五宫:大庙、宗庙、考宫、路寝、明堂。” [9]《通鉴地理通释·历代都邑考》亦载:“周公相成王,以丰镐偏处西方,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阳以即土中,遂筑新邑,营定九鼎,以为王之东都洛邑。”[10]
从上引文献可知,成王之世确有营建东都洛邑的活动,问题是周公所营建的洛邑究竟为一城还是分为王城和成周两个城邑,长期以来学界争讼不已,自汉代以来,就有两城说为多数学者所认同,但现有考古成果尚不能为两城说提供充分证据。李民先生的考证颇具启发意义,他认为,周武王时已有洛邑之名,周公营建洛邑时,亦称“新大邑”、“新邑洛”,成王亲政后称成周,终西周之世,洛邑、成周二者并名。及至春秋,“王城”之名起,但开始并不独立于成周,而是居于成周之西偏。析言为王城、为成周,统言则仍为成周。直到战国年间,东西两周分治,王城与成周遂分为两地。[11]若李民先生所说为事实,则西周洛邑确为一城。杜勇先生亦考证认为,周初营建东都,始称洛邑,复称成周。地在洛北涧东瀍西一带,亦即春秋时王城所在地。平王东迁,成周渐有王城之称,然二者兼用无别,长达二百多年。
洛邑又称成周。成周者,“周道始成而王所都也”。新建的东都洛邑,表示王业已经成就,故称“成周”。成周与宗周相对应,宗周之得名,皇甫谧《帝王世纪》指出:“武王自丰居镐,诸侯宗之,是为宗周。”[13]武王、成王、周公“封邦建国”,广封同姓诸侯和有功勋的异姓诸侯,建立一整套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政治统治机构,以便巩固已取得的天下,周天子为天下大宗,同姓诸侯为天下小宗,小宗尊拥大宗,维护王室,故有“宗周”之称。
二、洛邑的都城功能
洛邑的营建在西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古代政治史上亦是一个创举。武王、成王营建洛邑“居九鼎”,分设东西两都,这对于加强对中原地区以及对四方的管理和统治,创建强大的西周王朝,起了重大作用。
洛邑作为丰镐功能的延伸和统治东方的据点,发挥了都城的政治、礼仪中心职能。《尚书·诏告》说:“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14]周王受命于上帝,在中土洛邑统治天下的土地和人民。显然,营建成周的政治目的,就在于按照上帝“成命”在中土治理好小民。洛邑建成后,将象征国家的九鼎重器置于此,成王在成周大庙中举行朝会诸侯及贵族的“殷见”大礼,在考宫中举行祭祀盛典,庆祝成周大邑的建成。诚如《尚书大传》所说,“于卜洛邑,营成周,改正朔,立宗庙,序祭祀,易牺牲,制礼作乐,一统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诸侯,皆莫不依绅端冕,以奉祭祀者。其下莫不自悉以奉其上者,莫不自悉以奉其祭祀,此之谓也。尽其天下诸侯之志,而效天下诸侯之功也。”[15]举行“殷见”大礼,庆祝周王朝一统大业的成功,目的就在于宣布建立一种新王朝的统治秩序。自成王“肇称殷礼”以后,这种政治活动便在成周延续下来,《士上禾皿》所说“殷于成周”,《小臣传卣》所云“殷成周年”即此例证。这种集合四方诸侯以及群臣百官大会见并对上帝、祖先大献祭的殷礼,既对群臣具有督促考核的作用,又是检查诸侯是否尽忠述职的重要手段。《逸周书·王会》说:“成周之会,……天子南面立”,[16]诸侯前来觐见,亦见成周非政治、礼仪中心不足以当其位。周孝王时,成周八师征讨南夷,凯旋而归,俘敌四百人,周孝王在成周南郊大庙里举行庆功大会,嘉奖有功将士。周宣王时,曾以“会猎”为名,朝会诸侯于成周,为发动讨伐外敌的战争做准备。《国语·郑语》记史伯与郑桓公语云:“当成周者。
成周因其位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又成为西周王朝的东方财赋集中地。在整个西周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占据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对周围“郊甸”征发人力物力的中心,而且是对四方诸侯及被征服夷戎部落征收贡赋的中心,在稳定西周王朝经济基础方面起到了超过镐京的作用。因为歧周、丰镐位处西土,距东部广大地区路途遥远,且有崤函之险与东方相隔,四方贡物周转十分不便。洛邑居于天下之中,是四方贡物汇集的理想地。如西周铭文《兮甲盘》载:“王命甲征司成周四方责(积),至于淮南夷。淮南夷旧我帛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其进人,其各,毋敢不即次,即市……”[22]兮甲受周王之命居成周,负责征收管理成周及其周围地区的粮草委积,范围包括淮南夷地区。《颂壶》铭文载,成周有储存物资的仓库,囤积有大量东方与南方的委输。可见成周在西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中枢作用,是岐周和丰镐所不能比拟的。
三、成周与宗周的地位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关于成周与宗周的地位及关系,亦是一个长期争讼的问题。成王是否确曾迁都成周?成周与宗周是两都并恃?还是一主一辅?至今没有定论。
一般认为西周王朝实行的是以丰镐为首都的多都并用制度或主辅都城制度。宗周丰镐始终居于全国政治统治中心地位。岐周作为周人的发祥地,是文王受大命之所在,许多重要祭祀活动在此举行,被认为是周人的“圣都”,在整个西周时期都保持着崇高地位。洛邑成为都城是在周公成王以后,成王在洛邑以成功祭告祖庙后仍归镐京,而命周公留守洛邑,未曾迁都。正如司马迁所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23]至于迁鼎于洛,并非迁移都城,“至多是政治中心的暂时转移,原都邑仍然存在”,“西周的大多数时期,成周的地位甚至不如丰镐宗周和周原岐周”。[24]在传统观念里,西周时的洛邑只是一个陪都,在以宗周为主的主辅都城制中一直处于辅都地位。
周武王灭殷后建都于洛邑,而且把作为国家政权象征的“九鼎”放在洛邑。成王、周公都在成周执政,这既有文献可鉴,亦有出土实物可证。可见这时的西土镐京只是作为他们的老家(宗周),而成周洛邑则是他们统治中国的真正政治中心。[25]《何尊》铭文的发现及其不同的解读,似乎又为“成王迁都说”提供了有利证据。《何尊》说“: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丰)礼,裸自天。”说明成王确曾迁都成周。[26]更进一步说,成王既然即位于成周,就没有理由舍弃东都再把首都迁回关中。只是西周中叶之后国力渐衰,无力顾及东周,只能看守“老家”罢了。所以终西周之世,镐京(宗周)、洛邑(成周)是两都并存的。[27]以上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足见两都关系问题的复杂性。王健先生对两都关系的论述颇有见地。他认为,即使成王迁都,也并不一定放弃旧都,因为从史实看夏商周一直是数都并存,迁都之后并不一定放弃旧都。当时的确在东方新建了一个都城,可能是政治中心在某一时期(如周公主政时期)的暂时转移。王的某个时期转换居住地点,导致政治中心的暂时转移应是经常发生的事。周公营建洛邑,成王并没有长期居住于此,洛邑实际上是周公统治东方的军事基地。[28]周公之后,其子君陈继续居成周镇守。王健先生又引述日本学者伊藤道治的话说:“或许成王也曾一度决意永远居住成周,但是有一时期回宗周去了。从金文可以知道成王以下的诸王有时在成周逗留,但其根据地还是在宗周。这个事实可以说明,虽然西周王朝的人们知晓成周在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但作为生活基地的宗周对他们更具有吸引力。”[29]由此他得出结论:西周没有放弃宗周而迁都洛邑成周,洛邑成周也不是天下唯一的都城,整个西周的主要都城至少有西土的宗周、岐周和东方的成周三座,它们都应是天下的政治统治中心。[30]应当说,这一结论是正确的。营建洛邑并不意味着放弃其它都城,大量文献、金文及考古材料都表明,整个西周时期,至少有三座都城都在发挥着统治天下四方的政治中心作用,即宗周、岐周和成周。但对于成周在西周政治地理结构中的重要作用,似估计不足。诚如王健先生所说,在早期国家时期,由于地理环境在政治军事中的重要作用,一个都城是不能控制广阔疆域的,所以在最重要的地点,建立几个都城,王轮换巡视居住在这些都城中,以强化对四方疆域的有效统治。[31]就西周疆域形势而言,洛邑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所谓“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